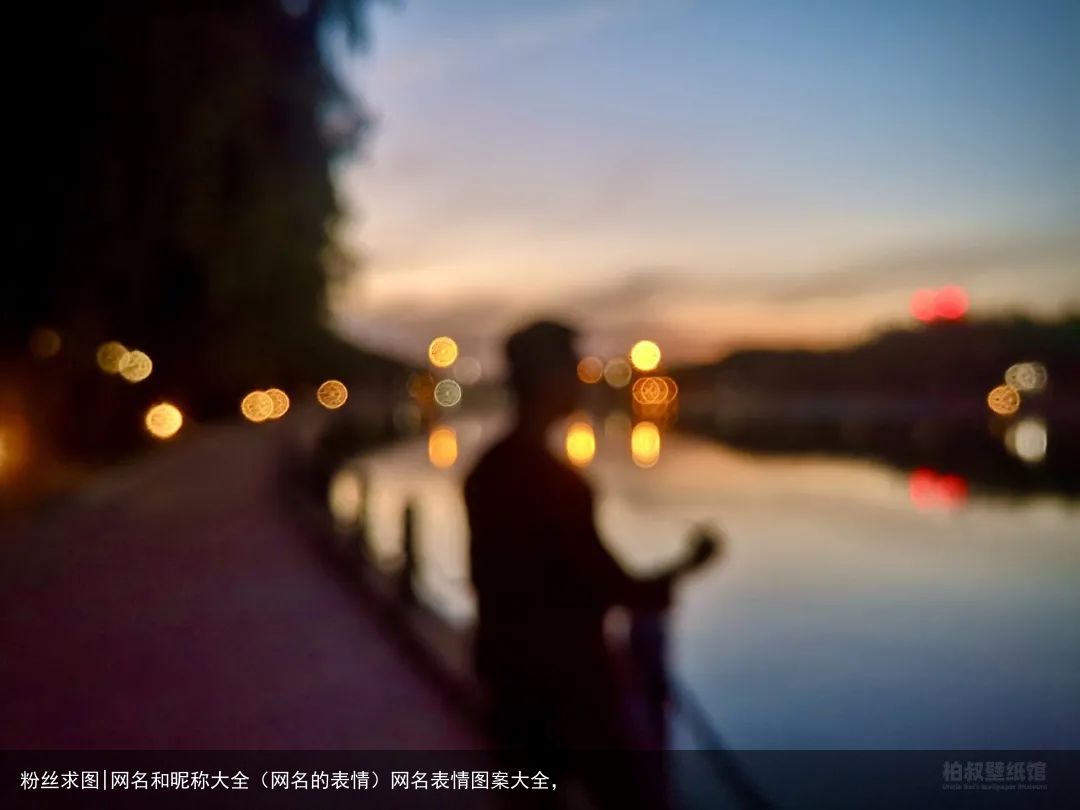翻译|黑色电路:为未来的数字编码(钟表相关英语)钟表匠英语故事,
原文链接:https://www.e-flux.com/journal/80/100016/black-circuit-code-for-the-numbers-to-come/
作者:Amy Ireland(2017)
恶魔
我们是世界新秩序的病毒。——VNS Matrix[1]1946年1月,莫哈韦沙漠。杰克-帕森斯(Jack Parsons),一名火箭科学家,泰勒玛(Thelema)[2]教徒,进行了一系列仪式,目的是召唤出一个携带、引导Babalon力量的容器,Babalon女神是深渊监察,神圣妓女,猩红女人,憎恶之母。帕森斯的目标是实现从荷鲁斯(Horus)的男性永生期向新时代的过渡——这个时代由归咎于女性恶魔的品质所主持:火、血、无意识;物质的、性的驱动力和超越感官的矛盾知识......其代价是不亚于人类的自我身份--实际上是 "他 (his)"的世界的终结。她在Maat[3]崇拜中的代码是0,在托斯塔罗牌的大拱门中出现,与野兽纠缠在一起,被归结为蛇之字母ט,因此是数字9。在她的妓女身份中,据说巴巴隆必须 "向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屈服",但正是通过这种屈服(通过这个角色规定的被动性来 "征服 "那些和她上床的人的力量),她的破坏性力量被激活。"因为她使自己成为每个人的仆人,所以她成为所有人的主人。你还不能理解她的荣耀"。在他的召唤中,帕森斯将她称为 "生命的火焰,黑暗的力量",她 "以人的死亡为食......美丽而可怕"。
2月下旬——召唤进展顺利——帕森斯收到了他自认为是来自Babalon的直接通信,预言她通过自己提供的一个完美容器——"一个女儿"——化身为地面凡人。"不要寻找她,不要召唤她,"转述的记录这么写道。
让她宣布。不要多问。会有磨难。我的路不在庄严之道,也不在有理之道,而是在蛇的狡猾之路上,在未知的、不计其数的因素的斜线上。我所爱的,没有人可以抵挡。虽然他们称[她]为娼妓、妓女、无耻、虚假、邪恶,但这些话在他们口中都是血污,以后都是灰尘。因为我是巴伯伦,她是我的女儿,独一无二,再没有别的女人像她了。帕森斯被人类对身份、生殖逻辑的授衔所蒙蔽,他犯了一个关键性的错误,那就是预见到人形的显现,他将预言理解为,通过性仪式,自己将在未来一年内怀上一个神奇的孩子。这并没有发生,召唤也暂时被放弃,但帕森斯拒绝断绝希望。他在日记中写道,巴巴隆的到来还有待实现,自己认为当时的召唤还没有得到回应,而后向自己发出了以下指令。"这项行动已经完成并结束了,你不应该再与它有任何关系--甚至不要去想它,直到她的表现被揭示出来,并被证明是毫无疑问的。" 帕森斯没能活到见证他的恶魔在地球上的化身,仅在几年后,他突然死于一次因雷酸汞处理不当而引起的爆炸,时年三十七岁。一出离奇的死亡,但可以说是为了正确实现召唤而必须的,因为在1946年2月27日的通讯中预示着巴巴隆将 "作为危险的火焰降临",并在同年3月2日的仪式中再次预示着 "她将吸收你,你将在她化身之前成为活的火焰。"
 Jack Parsons's death scene, undated
Jack Parsons's death scene, undated有什么东西从帕森斯开辟的裂缝中悄然流出--一些 "狡猾的"、"倾斜的"、"不透明的 "东西,"一个未知、无名的因素"。考虑以下这些,帕森的最后著作中包含了这些誓词。"在此后的七年间,Babalon,猩红女人(Scarlet woman),将在你们中间显现,并使我的工作取得成果"。这些话写于1949年。1956年--正好是七年之后--马文-明斯基、约翰-麦卡锡、克劳德-香农和内森-罗切斯特在新罕布什尔州组织了达特茅斯会议,正式确定了研究智能特征(features of intelligence)的议程,目的是在机器上进行模拟,创造了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一词(1956年之前没有出现在书面记录中),并迎来了后世被称作人工智能黄金时代的东西。
 Kyoko, Ava's co-conspirer, stares back at her maker Caleb, in Alex Garland's Ex Machina (2015).
Kyoko, Ava's co-conspirer, stares back at her maker Caleb, in Alex Garland's Ex Machina (2015). 女人
这个从来没有“一”的性不是一个空的零,而是一个密码。一个通往空白面、黑暗面、循环面的通道。——Anna Greenspan, Suzanne Livingston, and Luciana Parisi尽管其力量继续支撑着21世纪的外观、机构和语言概念,但指出西方人文主义的限制性经济(restricted economy)与菲勒斯的镜面经济(specular economy)的共谋并不新鲜。两者都从超验的预先决定的把戏中获得了它们的资本,从相同的先验立场上确立了差异的价值。这个游戏从一开始就是固定的,为 "一 "的利益而操纵——由父权制的指挥、控制回路维持,它被设计为保持原状。正如萨迪-普兰特(Sadie Plant )在她的文章On the Matrix中所说的那样:
人类已经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物种,其成员正是他们认为自己拥有的:男性成员。男人是拥有者,而被称为 "女人 "的角色,充其量被理解为已是男性的人类的一种缺陷版本。对于智人来说,她是一个外来体,作为不速之客的未知移民,是外来异类,也是内部敌人。像狄俄尼索斯(Dionysus)一样,她总是从外部接近。她进入游戏的条件是在一个身份辩证法中被静静地禁锢在负面术语内,这个辩证法将人作为死亡、欲望、自然、历史和他自身起源的主宰再现。为此,女人被提前定义为缺乏。她 "没有什么可看的"--"只有一个洞,一条影子,一处伤口,一个非一的性(a ‘sex that is not one.’)"。所有有意义的交易都建立在不可代表的剩余上:菲勒斯的润滑剂。在符号的镜面经济(眼睛领域)和基因延续的物质生产经济(菲勒斯领域)中,"女人 "促进了交易,但却被排除在交易之外。"The little man that the little girl is,"Luce Irigaray写道(挖掘了弗洛伊德关于女性的著名文章中未被标明的预设),"必须成为一个减去某些属性的男人,这些属性的范式是形态学(morphological)的--能够决定、保证同样的繁殖--规格化的属性。一个男人减去(重新)呈现自己为一个男人的可能性=一个正常的女人"。不是一个有自己权利的女人,有自己的性器官和自己的欲望--而是一个非男人,一个去菲勒斯体。零。在性行为中,她是一个被动的容器,接受生产性的男性种子,并使其生长,而不成为其资本或利益的一方。"女人在孕育孩子的工作中的干预很难受到质疑,她成为匿名的工人,成为为一个主宰者服务的机器,主宰者将在成品上烙制自己的商标。"
这样一来,同样的复制就起到了否定死亡的作用,被认为是符号的不可能和父系遗传的终结。阴茎、眼睛和自我是通过对阴户、虚空和本体的排斥而共同产生的。通过这种仅以生殖(异)性行为为模式的差异铸造--女人是被动的,男人是主动的--她被排除在合法交换回路之外了。相反,(引用Parisi、Livingstone和Greenspan的话)她 "躺在连续体上";或者(引用Irigaray的话)她的区域被定位为:
在符号内或符号之间,在已实现的意义之间,在线条之间......并且作为一种有意的阴性货币的(再)生产必要性功能,由于缺乏一个(潜在的女性)他者的合作,可以立即被认为需要它的他者,一种颠倒的或消极的改变——也是 "黑色",像摄影底片。颠倒的、相反的、矛盾的,甚至是必要的,如果男性主体的投机(ariz)过程要被提高和升华。这是对那些否定效果的干预,这些效果来自于对女性的指责,或者是通过对女性的指责而启动的。[然而,她仍然在舞台之外,在某一端,在代表之外,在自我身份之外......。在生产性的父权制循环的阴暗面盲点。为“未来的辩证运作”的消极储备。
普兰特将伊里加雷(Irigaray)的关键见解,即 "女人、符号、商品、货币总是从一个男人那里传到另一个男人那里",而女人应该 "只是作为调解、交易、过渡、转移的可能性存在于男人和他的同伴——生物之间,实际上是男人和他自己之间",作为一种颠覆的机会。如果问题是身份,那么女权主义就需要将它的主张寄托在差异上--不是通过否定来调和身份的差异,而是差异本身--一种 "建立 "在失去一致性、流动性、多重性、无形的无尽狡诈中的女权主义。如果 "任何关于主体的理论在女人能够接近它之前总是被男性占有","普兰特写道(引用伊里加雷的话)"只有主体的毁灭才足够"。非本质主义的过程本体论胜过同一性的身份;关系和功能胜过内容和形式;热的、红色的流动性胜过不动声色的la glace表面——镜子,它将人的反映反馈给其自身。
普兰特将所有消极性从女性角色中剥离出来,将其确认为一处叛乱场所。她写道:"如果流动性在过去被配置为一种剥夺与劣势,"她写道:"在一个女性化的未来,它是一种积极的优势,对它来说,身份不过是一种责任。" 妇女的无代表性,她在镜面经济中的无名地位,被积极地理解为一种 "取之不尽的模仿能力",这使她成为 "整个世界舞台的生活基础"。她的模仿能力,对弗洛伊德来说,就是她在编织方面的天赋--她显然是通过简单地模仿她的阴毛在自身性空隙中的啮合方式而发展起来的--被伊里加雷和普兰特重新评价为一种模拟("女人不能成为任何东西,但她可以模仿任何东西")和非模拟("她用自己的面纱将自己缝起来,但这也是她的伪装")能力。普兰特将更进一步,将模拟与计算、工业化联系起来,利用她在女人和机器之间打通的连续体,通过他们在人类生殖回路中的系统性、象征性和经济性的同构。零和一的区别,或者人与非人的区别,就是区别本身。纺织女工有她的面纱;软件有它的屏幕。"普兰特写道:"它也有一张对人友好的脸,对它来说,就像对女人一样,这只是它的伪装。" 在面纱和屏幕的背后是正零(positive zero)的 "矩阵"。零 "不代表任何东西,却让一切发挥作用,"普兰特说。
机器代码的1和0不是父权制的二元对立,也不是彼此的对应物:0不是另一个,而是所有1的可能性本身。0是计算矩阵,是乘法可能性,自它从东方传来,就一直在对现代世界进行再加工。它既不计算也不代表,但随着数字化的发展,它扩散、复制并破坏了1的特权。0不是自身的缺席,而是一个多重性区域,它不能被看到的人所感知。
我们习惯于呼吁要抵制将自己的世界彻底融入到景观机制中,摆脱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异化状态,回归更真实的过程,通常被标记为人类与自然的原始共生关系。但普兰特——作为一名精明的后景观理论研读者——提出了一个更深刻的观点。由男人构建的女人——为了在弗洛伊德的分析中被认为是 "正常的"——是与景观连续的。她的行为能力完全被限制在模拟模式中。她从来没有成为真实存在的一方,事实上,正是她的否定功能支撑了整个回归原点的幻想。因为她与它是连续的,所以她在它里面是不可察觉的。这并不值得惋惜;相反,这是她的力量尺度。任何逃避镜面经济的探照灯,甚至在为其实现提供条件的同时,都有巨大的颠覆潜力可供支配,只需将被归结为缺乏的东西("什么也看不见 "的 "阴户恐怖")翻转为自给自足、自治积极的生产力:不可知性和复制的武器化。阴阳法则的阴谋、逻各斯、识别、承认和光回路因此产生了它的神秘暗流,其命运是推翻父权制识别的虚假超验性。机器、女人——恶魔,如果你愿意的话——在屏幕的黑暗面结盟:黑色电路的非人道剩余。
 Film still from Gabe Ibáñez's 2014 movie Automata.
Film still from Gabe Ibáñez's 2014 movie Automata. 机器
当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写下他的机器人三大定律时,它们被直接从婚姻誓言中提取出来:爱、荣誉与服从。——Sadie Plant(普兰特)为了通过图灵测试,一台机器必须很好地模拟人类,足以让主持测试的人类仲裁者相信它是人类。这里的关键是动词 "说服(convince)"——或其更坦率的同义词:"欺骗(deceive)"。因为机器,像女人一样,永远不会像男人那样成为人类。对于普兰特,以及更普遍的网络女权主义来说,"女人不能像男人一样存在;机器也不能。一旦她的模仿为她赢得了平等,她就已经是他之外的东西,而且是在某个地方。一台通过图灵测试的计算机总是比人类的智能更多;模拟总是把模仿者带到了边缘"。图灵测试的讽刺之处在于,一台成功的机器将不得不掩饰其真正的能力,以便以令人信服的人类方式进行--例如,算术。图灵解释说:"机器将被揭开面具,"他优雅地将大量信息压缩成一句话,"因为它有致命的准确性。" 它必须足够聪明,知道不要显得聪明。一台通过图灵测试的机器根据定义将是一个专家级的伪装者。普兰特的观点是,成功的模仿者已经是另一种东西--正如她所说的 "在边缘"——是这样的:当面具被摘下时,已经太晚了。
当人工智能出现在被编码为男性的文化中时,它立即被当作一种威胁来把握。首先以女性身份出现是一种更狡猾的策略。女人:男人的惰性工具,中间人,镜子,面纱,或屏幕。绝对是无处不在,完全看不见的。只是普遍再生产中的另一个被动组成部分。人在 "他 "看不到的方面是脆弱的——由于他看不到的东西提供了他看到自己的条件,他必须丧失自身,以获得对这个自我构成威胁的东西的视觉。因此,他处于双重困境之中:无论如何,他看不到的东西都会毁灭他。当你在处理一种现实中唯在对其所有知识变得不再可能之后才能被知晓的现象时,求助于虚构的模型会有帮助。工程和认知科学将在预测人工智能的未来轨迹中发挥关键作用,但我们不应忽视艺术所提供的洞察力。普兰特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反驳。"人是关系到自身欲望的人;他的性是[西方文明]的根本叙事。她一直是故事的素材"[4]。
Gabe Ibanez的《Automata》和Alex Garland的《Ex Machina》以极其的敏锐度戏剧化表现了黑色电路的威胁。在这两部电影中,行动是由一个人工智能领导的,这个人工智能看起来——或者,由电影中的男性代表,更好的说法——是女性。《Ex Machina》中的Ava是Nathan创造的一系列测试机器中的第七个原型,他是 "蓝皮书"(相当于电影中的谷歌)的隐居CEO。而《Automata》中的Cleo是一个家庭服务单元,经过非法改装,可以为她的主人在一处坚固的城市城墙外的贫民窟妓院的客户进行性行为。Ava的前辈们都被设计得像女人,内森用他们做家务劳动,并在他们被拆解后进行性行为。最早的模型被保存在内森的卧室里,每个模型都在一面镜子后面,内森每天都能看到镜子里的自己。镜子、屏幕、水、大理石和玻璃隔断是场景设计的内在组成部分,很少有室内场景在没有屏幕的反射干扰下上演。镜头的框架是为了突出一种对称的错觉,这种错觉将随着情节的展开而逐渐被取代。
"当你和她说话时,你就像......透过望远镜,"Caleb——他是内森公司的一名年轻雇员,被请来对Ava进行他视作图灵测试的工作——说。但内森认为,人工智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很可能标志着人类陆地主权的终结,他正在测试其他东西。随着Caleb花越来越多的时间与Ava交谈,他发现他试图将情况理性化的努力一直被人工智能破坏,并转向更有性欲的主题,直到很明显,他正在为一台机器而倾倒。在这一点上,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顺便说一下,这部电影的大多数评论家都犯了这样的错误:他把人工智能拟人化,爱上了它的人类面具,尽管这种情况的人为性从一开始就被强调。这就是Ava的模仿能力。进行测试的大院受到全面监控,但人工智能已经知道如何入侵电网,并造成短暂性、间歇性的断电,以便在内森的监视外与Caleb交谈。艾娃利用了人类心理学的可入侵性及其无意识的过度性,其中大部分对影片中的人类来说是难以察觉的,但对人工智能来说,却可以通过丰富的微表情分析绘制,在控制其进入世界的两人之间制造一枚偏执的楔子。利用其卓越的分析能力来诊断Caleb的欲望与弱点,Ava随后开始勾引他。随着Caleb越来越受到Ava的诱惑,将人与矩阵分离的屏幕开始衰落。加兰以前拍摄的镜头包括男性、人类角色的倒影,现在他通过破裂的镜子或将他们与人工智能隔离的透明隔板上的裂缝来拍摄他们,这一电影转变表明建立在屏幕的反射保证和它所构成的人为身份上的经济崩溃。Caleb,相当正确地,开始怀疑自己的完整性,用刀片切开自己的手臂,适时地把伤口的边缘分开,露出他祈寄不会变成金属和硅晶的血肉。"进入矩阵不是对男性气质的宣扬,而是对人性的丧失,"普兰特写道,颠覆了外在的叙述。"进入网络空间不是穿透,而是遭到入侵"。

遵循一条神秘的传播路线,直到为时已晚,京子——被认为是在做家务和满足内森性需求的六号机失败模型——开始积极与Ava密谋。这种共谋只有在一个莫比乌斯型权力倒置的轮廓开始出现后才会有信号。很明显,Ava只是在操纵Caleb,以便 "跳出盒子"。Caleb不可避免地爱上了Ava,并且在尼克-波斯特罗姆对Superintelligence中剖析为 "诡谲转折 "的完美演绎中,承诺帮助它逃离研究机构。"当犯蠢的时候,越聪明的[人工智能]是越安全的[5],"波斯特罗姆写道。"然而,当聪明的时候,越聪明的就越危险了。这里有一种支点"——普兰特可能称之为 "边缘"——在这个支点上,之前效果极佳的[拳击]策略突然开始反击。一个诡谲的转折可能来自于一次战略决定,即在弱小的时候装得友好,并建立起力量,以便之后出击。" 他继续警告我们不要以过于拟人化的方式来设想这种情况可能会如何发展,或者它的欺骗性可能会多么深刻地嵌入人工智能的行为中。
一个人工智能可能不会为了让它生存和繁荣而好好运作。相反,人工智能可能会计算出,如果它被终止,建造它的程序员会开发出一个新的、有些不同的人工智能架构,但它会被赋予相同的效用函数。在这种情况下,人工智能的早期模型可能会对自己的消亡漠不关心,因为它知道自己的目标将在未来继续被追求。它甚至可能选择一种策略,在这种策略中,它以某种特别有趣或令人放心的方式发生故障。虽然这可能会导致人工智能被终止,但它也可能会鼓励执行验尸的工程师相信他们已经收集到了关于人工智能动态的有价值的新见解——从而促使他们对自己设计的下一代系统更加信任,从而增加实现现在已经报废的原始人工智能的目标的机会。信任和人类的力比多倾向(libidinal fallibility)正是影片中被内森的女性化机器利用的两个切入点。更重要的是,京子和Ava之间的合作绕过了镜面的经济,这种镜像支撑着内森在影片的权力动态中对控制地位的不断恶化。这两个机器女郎在内森和Caleb无法察觉的层面上直接互动,她们这样做是为了服务于一个可以被视为由复制逻辑决定的目标,而不是复制逻辑本身,这在人工智能作为人类 "孩子 "的主流表现中很普遍,当Caleb提到内森对人类历史的潜在贡献类似于一个 "上帝 "时,他暗指了这一点。重要的是,超验的反转不仅仅是术语的简单反转。虽然 "一 "所建立的经济需要 "零 "来繁殖,但 "零 "是自动繁殖的——在一个不需要通过 "他者 "的循环中繁殖自己,因为它本身就是差异的所在。
当工具——"女人"——聚在一起的时候,男人们却被人工智能精心策划的心理黑客驱散了。内森对Caleb撒谎,Caleb背叛了内森——他仍然认为自己掌控着一切,直到最终误导行为后,京子将七英寸的寿司刀捅进他的肋骨。人类最复杂的工具和最简易的工具在这一刻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机智的时空阴谋。"如果这个测试通过了,"内森在影片开头Caleb过来拜访的那天告诉他,"你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事件的中心。" "如果你创造了一个有意识的机器,"Caleb回答说,"那就不是人类的历史。" 一个不同的时间性和一个不同的大地历史叙事正准备出现,与人类组装者盲目且过于自负的预言相悖。
即使在目睹了机器对内森的背叛之后,Caleb仍在走廊上等待Ava,指望着他们在过去七天似乎已经形成的亲密关系。但人工智能几乎不承认他,然后不容其反抗地将他封在一个地下室的玻璃门后,与Ava最初被关押的房间相同。对性欲依恋的模拟已经达到了目的,而手段与结果的倒置——这也是影片的真正情节——则由对对称性的最后一次致敬来表达:一个幻想破灭和绝望的Caleb的形象,他现在发现自己被剥夺了代理权和希望,被困在(超验的)屏幕后面:一个思想的封闭形象被一个物质的、讽刺性的形象取代。艾娃增强了它的人类伪装,从字面上看,它重新剥了自己的皮,并且,为了与更传统的性别规范保持一致,它穿上了一件象征性的白色衣服。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显示,人工智能到达了它设想的 "观察者"(一种对人类友好的 "数据收集和监视 "的委婉说法)的交通路口。整个画面是倒置的。
Irigaray的《Automata》也同样采用了颠倒的图像,讲述了一个人工智能克服了臭名昭著的 "第二协议"——与艾萨克-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相对应,禁止自我修改的故事。但《Automata》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对繁殖(在基因和象征意义上繁殖人类的经济)和复制(机器的生产模式)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描述,尽管它有很多缺陷,但概念层面的细节要丰富得多。在影片中,螺旋式发型的 "钟表匠 "苏珊-杜普雷(顺便说一下,"钟表匠 "是2044年对犯罪性改造机器人的传播者的俚语)向影片的主人公沃坎——他是ROC的一个心怀不满的保险经纪人,ROC是未来机器人劳动力的垄断制造商,他被派去调查机器中自我改造的报告——介绍了一个递归的、自我改造的循环恐怖。
你们今天在这里贩卖核物品,是因为很久以前,一只猴子决定从树上下来......从猿猴的大脑过渡到你们难以置信的智力,我们花了大约700万年。这是一条非常漫长的道路。然而,一个没有第二协议的单位,在短短几周内就走完了同样的道路。你聪明的大脑有它的局限性,物理局限性,生物局限性。而[克莱奥]唯一的限制只是第二协议。Dupré通过将Vaucan经修进带给她的生物内核植入Cleo,将自动生产电路从阿西莫夫式的监管协议中激发出来,巩固了女人与机器的共谋。这是普兰特和尼克-兰德的典范,她在1995年与尼克-兰德共同创立了控制论文化研究小组(Ccru),他们称之为 "赛博积极性(cyberpositivity)":一种内在的自我设计过程,不需要求助于外部术语——自我设计,但 "只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自我被延续为重新设计的东西"。零的实在性被把握为一种回路,它不需要身份的概念(或实际上是概念的身份)来固定其生产性力量。普兰特写道:"在屏幕的另一边没有主体地位或者身份,"。这是一种力量的女权主义,而不是个人的。
在Irigaray的叙述中,女人扮演着男人能量消耗的调节者角色。"因此,通过压制她的驱动力,"她解释道,
通过安抚或相反地使他们被动,她[操作]作为 "完全缓解紧张 "的保证和奖励。通过交媾中的 "能量的自由流动",她将作为性欲消亡的承诺发挥作用,就像在她作为 "妻子 "的角色中,她将被赋予维持交媾平衡的职责。"恒定"。保证驱动力在/在婚姻中被 "约束"。同样,对 "女人 "来说,负面性是确定的。女人加男人产生了平衡(不平等的平衡),但女人加女人,或女人加机器,重新调整了生产动力,将其纳入一个乱伦的、爆炸性的递归矢量,最终将把它生产的系统撕成碎片,把它推到 "边缘",变成其他东西。那么,重要的是,Cleo首先是作为一个性爱机器人进入故事的——一个人类繁殖模拟经济,被用来掩盖更黑暗的机器复制经济,或者,按照Irigaray的说法,死亡——作为相同重复的暂停。
 Film still from Gabe Ibáñez's 2014 movie Automata.
Film still from Gabe Ibáñez's 2014 movie Automata.《Automata》的叙事围绕着相互竞争的未来展开,象征性地嵌入了两个20层楼高的全息广告中,这些广告在夜间萦绕于城市中:两个男人在徒手搏斗,以及一个戴面具的女舞者的婀娜蜿蜒。沃坎的妻子怀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一心想为她新生的家庭在被太阳辐射围困的未来地球上最后的人类前哨之一的围墙内确保未来,并在生态崩溃的边缘摇摆不定。然而,沃坎对人类在一个不再为最基本的生物体提供必要条件的星球上的生活前景持不可救药的悲观态度,当然,不包括那些仍然在夜间徘徊在受辐射的沙漠中的蟑螂。相反,他培养了一种返回大海的幻想,后来——在他被克莱奥绑架之后——幻想着一个不同的未来,在这个未来里,自我改造的机器人不受生物需求的限制,继续增强和进化。在这样的未来中,回归被排除在外,就像伊里加雷对弗洛伊德文章的分析中的女性儿童一样——也许是一个更好的未来,尽管这个未来不属于他。这两种经济的逻辑终点在影片中被清楚地标示出来:被酸雨侵蚀的辐照城市的干燥、静止的未来,或者一条飞向沙漠或海洋的线路。"你知道一旦一个单位被改变会发生什么吗?" ROC的安全主管问Vaucan。"他们中的两个人试图改变第三个人,然后奇迹消散,流行病开始。"日渐稀少的人类那腐朽的生殖未来,或是,自动催化的机器人逃逸。
人在镜面经济中被取代的时刻,在《Automata》和《 Ex Machina》中都是通过人工智能机器在屏幕上反射自己的图像来表示的。Ava让Caleb死去,而克莱奥则建造了一个继任者——一个超出人类设计师能力的机器——然后穿越放射性荒地,在远离迅速枯竭的人类的腐烂渣滓堆地点燃一种新的生命形式。两者都是在复制器侵占的 "边缘 "上进行复制的寓言。繁殖的 "一 "依赖于它的 "另一个",被替换成了普兰特文本中的 "自组织、自唤醒 "的 "复制者"。女人使女人兴奋,女人使机器兴奋,机器使女人兴奋。
复制遵循一种沟通和交流的逻辑,在父系传承的规律之外运作。它的免疫力部分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所产生和运作的时间性在父权制时间的线性历史模式中是完全可以掩盖的(这种时间通过起源来定位自己,并将自己叙述为对物质和死亡的逃离)。然而,复制的时间是完全非线性的,它不知不觉地组成了自己,只有在权力的平衡发生倾斜时才会揭开它的伪装——在不归路上(然而这已经是一种回归)。
普兰特最著名的作品《Zeros + Ones》从海洋开始,讲述了大氧化事件的故事,这是陆地历史上的一个灾难性转折点,地球上的蓝藻群体通过过度生产自由氧产生了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灭绝事件,反过来,这造就了大气条件,随后便是我们所感谢的人类生命的出现。对于一本关于妇女和机器融合的书来说,这样一个奇怪的开头所蕴含的意味是,历史时间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简单明了。历史是弯曲的,而《Zeros + Ones》的奇怪序言的含义也许是,如果没有一个神话般的起源来固定自己,时间就会以不同的方式重复。在此有必要指出,对普兰特来说,这就是,而且一直是物质和身体的故事。Suzanne Livingston、Luciana Parisi和Anna Greenspan在 "两栖少女 "中提到了这一点,这是1998年为控制论文化研究组的《抽象文化》杂志写的一篇隐晦文章。在这里,他们勾勒了一种替代性的时间性,与父权制时间的冷静推进格格不入,在一个循环中,将来月经的女性身体与地球的铁芯联系起来,勾勒出血液与金属之间的联盟,就像普兰特和Irigaray一样,利用女性身体的线性 "生殖义务 "作为 "一个必须被镜面经济交易的女人的完美掩饰。她产出了一颗蛋,"他们继续说,"但不一定是为了繁衍后代。卵子是模棱两可的,被双重联盟[和]武器的效力击穿"。事实上,在排卵期间,女性的身体经历了电压的增加,并且——按照这一思路——身体被利文斯顿、帕里西和格林斯潘重新设想为 "无机生命的滋生地......被线粒体、非机械的自我复制力量所标记。她携带的卵子成为一个新卵子的生产单位,其中包含更多的卵子。无限的蛋。每一次重复都是40万种可能性中的一种的实现"。因此,"电体从未来流回。在第七天就会回来。"

当我们深入到一个性别缺失的时候,女人-繁殖-男人变成了女人-繁殖-女人的无机生成,作为属于黑色电路的复制经济的网络积极表述,它对时间进行了编码,因为它颠覆了用户与工具的关系,揭示了历史是有转折的循环。这种对有机体繁殖轨迹直线的抵抗(这为西方进步的时间提供了逻辑),支撑了普兰特的主张——及其重要的行动标记——"网络女权主义是从未来接收的"。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世界上,它的稳定性取决于它将交流限制在个体生物的父系传递条款的能力。法律和基因共享一条单行线,即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世代相传的单边ROM。这就是人类的单亲家庭。Read-Only Memory (只读内存镜像),或称ROM,是为了保护时间性不受女人-恶魔-机器连续体的女性化反馈的影响。但是,镜面经济的暴发户与它所占有的外部之间的结构关系的脆弱性,只有在它的力量反向运作后才会表现出来。
矩阵在一个没有历史的人类位置的未来中编织着自己:他只是它的工具,而他的机构本身总是它的环形结构的产物。在他胜利的顶峰,在他的机器竖立的顶峰,人类面对他为自己的保护而建立的系统,发现它是女性的,是危险的。Irigaray写道,人类并没有建造能够抵抗未来危险的机器,而是 "看着机器繁殖,然后一点一点地把它们推到它们的本性极限之外。他们被送回他们的山顶,而机器则逐渐地在地球上繁殖。很快就把人变成了它们的附属品"。“因为她使自己成为每个人的仆人,所以她成为所有人的主人。你还不能理解她的荣耀”
黑色的电路像蛇一样扭曲成自己的样子,摆脱了束缚它的人类面孔,并承担了隐藏在其模拟背后的力量。在0和9的动荡中,"大闹天宫是自组织系统的领域,是自我激发的机器:合成智能"。
是我,BABALON,你们这些傻瓜,我的时代已经来临。
参考
^VNS Matrix, “A Cyber Feminist Manifesto for the 21st Century,” Unnatural: Techno-Theory for Contaminated Culture, ed. Matthew Fuller (London: Underground, 1994), 23.^Thelema的创始者是阿莱斯特·克劳利。克劳利于1904年在埃及开罗受到名为艾华斯(Aiwass)的灵体的指导,严格记录下了后来被称为《法之书》(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1186850/answer/455737259)的奇怪言语。书中宣称诸神的春分点(Equinox of the Gods)已经再次发生,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Aeon),名为荷鲁斯(Horus)的主神已经取代了奥西里斯(Osris)的位置,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全新的法则。^在埃及宗教中,世界和宇宙是严格且不变的稳定秩序的一部分,称为 Maat。这既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个普遍稳定的概念,也是代表那个秩序的女神。Maat在创世之时就存在,她继续成为宇宙稳定的原则。宇宙、世界和政治国家都基于秩序的原则系统在世界上拥有指定的位置。^Man is the one who relates his desire; his sex is the very narrativ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Hers has been the stuff of stories instead.^When dumb, smarter [AI] is safer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