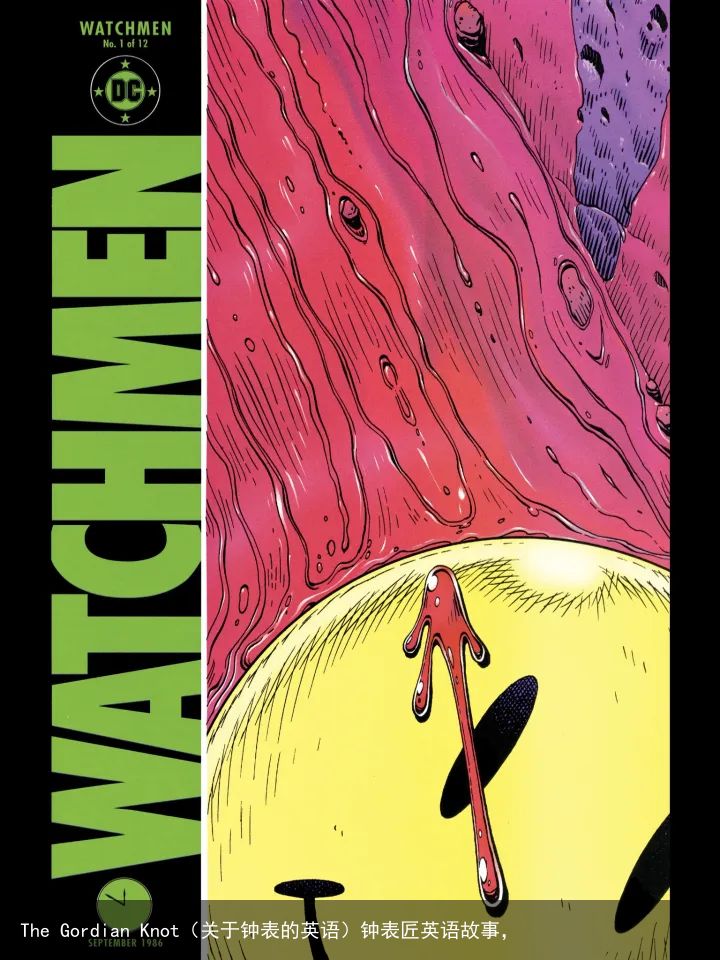闲聊清代自鸣钟表之舶来(钟表故事手抄报)民间钟表故事,
本文将挖掘并呈现一些自鸣钟表的历史记录和片段,希望让读者可以有针对性地了解一下西洋自鸣钟表舶来中国的经过及背后的一些历史。目的是为大家(特别是钟表爱好者)提供深入浅出和具有聊天意义的阅读素材,从而增加钟表收藏和分享的趣味性。
开端
坊间普遍认为西方机械自鸣钟是由利玛窦神父(Matteo Ricci,1552-1610)在明代(1368-1644)万历十年前后,即1582年左右带到中国来的。这种看法具有正史般的说服力,但也有一些历史学者持别样的观点。殖民地作家Carlos Augusto(1863-1927)在他的 Historic Macao(1902)一书内曾提到澳门的葡萄牙商人从明代就开始将欧洲的自鸣钟进口到中国,而时间上比利玛窦神父抵澳要更早。
机械计时器在欧洲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公元十二世纪,到了十五,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计时器已经有了广泛的应用,大至城邦内的教堂和钟楼,小至贵族的宅院寝室甚至长途马车也会配备。在需要远航的大船上,计时器就像今天的GPS一样重要。可以想象早在1511年就抵达珠江口外伶仃岛的葡萄牙商船(也可能是海盗船),就已经配备了机械的计时工具。
众所周知广州是清朝(中后期)的唯一对外通商口岸,但海禁的做法其实明朝就已经开始。明朝也曾有过“一口通商”,而这个地方史书上点出的是福建漳州的月港(即海澄县)。万历年间的《露书》有载:“近西域利玛窦作自鸣钟,更点甚明,今海澄人能效作,人谓外国人巧于中国,不知宋蜀人张思训已为之,以木偶为七直人以直七政,自能撞钟击鼓矣。” 就是说西洋的自鸣钟,宋代的张氏就已经能造,无需从洋媚外之意。中国最早的机械时计水运仪像台的发明人宋代的苏颂就是福建漳州府人,也许他在家乡留下的遗产远比官方记载的多?
人民大学的清史研究所曾发论文,认为中国最早的自鸣钟表可能来自明代的福建漳州地区,这个说法对应的是明史。据永乐年间史书载,葡萄牙和荷兰船只在这个时期到访了台湾、福建的金门和漳州等地。我们都知道,在风帆的时代登岸后船员的首要任务就是对船只进行修补。有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欧洲人需要维修船上的钟表时计,所以找来中国本地的工匠帮忙,又或者是当地人看到了洋人带来的“新玩意”直接就开始模仿制造。实情有待考究,但机械时计舶来的年代推前到明代前期的观点不是没有可能。爱新觉罗·昭连(1776-1830)在他的《啸亭杂录》载:“泰西氏所造自鸣钟表,制造奇邪,来自粤东,士大夫争购,家置一座,以为玩具”。粤东和闽南其实属于同一地区。
不论谁先谁后,我们无需从考古的角度切入本篇。笔者认为真正启动自鸣钟表舶来时代的是清朝的乾隆皇帝,因为这位腐败的皇帝是一位真正的钟表玩家和收藏家!也正是他,一手缔造了自鸣钟表的神话,成就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收藏巅峰。
大致上,康熙(1661年即位)在位期间,皇帝积极研究强国之道。他对机械计时器的态度见于他的《咏自鸣钟》:“法自西洋始,巧心授受之。轮行随刻转,表指按分移。绛帻休催晓,金钟预报时。清晨勤政务,数问奏章迟。” 康熙将自鸣钟当作一个很有用的工具,协助他将工作时间安排得妥妥当当,但仅此而已。雍正执政的时间较短,无需多做考研。乾隆(在位60余年)时期的自鸣钟包括舶来的,广作的,苏作的,都大放异彩。到嘉庆时代,皇宫的钟表采购基本结束、而民间怀表开始变得普遍。本篇主要研读弘历中后期与十三行关联的情况,因为彼时广州是大清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也是钟表舶来的必经之地。难度在于年代跨度较长,资料甚多但比较零散,学界和坊间的说法云云等。
钟表舶来之 - 十三行的贸易
稀珍大半出西洋,番舶归时亦置装;
新到牛郎云光缎,边钱堆满十三行。
- 《南海竹枝词》
清朝的一口通商政策实施于乾隆二十二年,西历1757年。这一年,英国的钟表大师 Thomas Mudge 发明了他的杠杆式擒纵系统(Lever Escapement)。就在这同一时期,伦敦的钟表珠宝商 James Cox 开始接到了一个又一个来自东方的订单,而且每一张订单都价值不菲!
据《国朝柔远记》所载,乾隆二十五年,在粤的行商有26家;《粤海关志》所载的为20家,但另有8家海南行。据英国东印度公司记录,在1765年的贸易季度,有以下行商与其贸易:
同文行,潘氏; 泰和行,颜氏; 广顺行,陈氏;
义丰行,邱氏; 聚丰行,蔡氏; 源泉行,陈氏;
逢源行,蔡氏; 裕源行,张氏; 广源行,叶氏。
(*大家较熟悉的巨富行商伍氏,要到乾隆晚期才崭露头角)
1759年,为了应对英国东印度公司新成立的特别‘议价’委员会,并保证茶叶的出口价格与质量,避免同行竞价导致恶性竞争做成烂市,由同文行潘氏(也有史料认为是聚丰行蔡氏)牵头,协同九家有实力的行商向朝廷呈请设立公行(联合行)。同年,John Harrison的航海时计H4问世,正是这项发明为英国奠定了走向海上世界霸权的重要一步!
公行成立将原有的二十余家商号划分为三个梯队。一级梯队专办欧西货税,谓之外洋行。二级梯队为本港行专管南洋之贡地(附属国)等贸易纳税之事。三类改原有海南行为福潮行,输报粤省潮州及福建货税。自此,十三行的主力军开始转向专对欧洲诸国贸易的时期,等于说西洋珍品的流入渠道集中到一块了。这个时期每年来华贸易的欧洲商船约为20-30艘,载重从150吨至500吨不等。
出口茶叶,瓷器和丝绸是我国的专利,但入口呢?下面看看清朝的国人都青睐哪些洋货,列出的为同文行 1766年的洋货输入名录:
琥珀,阿魏(西药,止抽筋),珍珠贝,象牙,鱼肚,人参,蜂蜜,槟榔子,海参,鱼翅,皮货,燕窝,樟脑(gomphor),冰片(barroos),丁香,洋红,棉花,儿茶(cutch),黑檀,桃花心木,檀香木,燧石,锡,玻璃器,豆冠花(mace),金属类,肉豆冠(nutmegs),乳香,胡椒,金青,木香(putechuck),水银,藤,沙谷米,白檀,苏木,毛织物等。
(*资料参考《十三行考》梁嘉彬)
主要都是一些需要加工的原材料,有木材,药材,香料,补品,纺织品等等。这是英国人绞尽脑汁才弄出来的清单。鸦片泛滥之前欧洲人根本无法扭转对华的贸易差。他们想尽了方、设尽了法,也曾尝试用昂贵的钟表来抵消入不敷出的差额,但到最后还是没辙。这种情况极大地鼓励了灰色贸易。粤海关的纵容、朝野贪腐风气的盛行、海盗的猖獗都导致了清代严重的走私问题。
史云,鸦片,象牙,棉花,水貂皮,胡椒和奢侈品等都是进口走私的热门选项。而出口朝廷明令禁止的黄金和超额的生丝也是屡禁不止。虽然大清的贸易是以白银为结算单位,但行商与外国人以货易货的情况则是常态。其实许多外国商人宁愿向粤海关隐瞒船上携带的西银(来自吕宋的西班牙白银)数量,从而为其在离开前采购走私货品留下购买力。当买卖回归到以物换物为基础的时候,皇帝喜爱的自鸣钟自然成为填补资金缺口和借贷抵押的优先选项!
据史载,1766年7月,税馆胥吏在西江河道逮到了一名丹麦和一名英国船长,他们试图用一只来自澳门的中国舢舨将价值昂贵的自鸣钟运到广州。这很显然是走私,当时的澳门虽然只准许挂葡萄牙和西班牙旗的商船停靠,但由于税率和汇率都比粤海关低,所以很受散商和走私客的欢迎。这两位船长算得上是珠三角最早的“水货”佬了!而这起事件,其实只是冰山的一角。整个十八世纪,葡萄牙人,英国人以及让人讨厌的巴斯人(包头的印度X)都在澳门积极地做着走私黄金,鸦片和贩卖人口等罪恶的勾当。
总的来说,就如维基百科对十三行的评价:“清朝统治者授予行商以外贸特权,但也从他们身上取得更多的财富,每年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监督进贡各种珠宝珍玩,如钟表,花瓶,珐琅器皿,雕牙器皿,日晷等.....俱令洋行采办物件,赔垫价值.......积习相沿,商人逐行苦累。”
钟表舶来之-上岸
乾隆初期,有位粤海关监督名叫李永标(1751-1759在任),英国东印度公司对这位监督意见甚大,在写给一名公司船长(Captain Parker)的信里曾这样警告到:“最近来了一个新监督,非常严厉,给行商造成极大麻烦,害得他们都拒绝担任我们的保商”。这位李监督下令让自己的亲信对每一条外洋货船进行详细的检查,导致已经在海上漂泊数月疲惫不堪的洋船被迫排队受检,而且一等起码半个月。虽然这个做法引起了许多怨言和不满,但它的合法性压住了所有人的情绪。但另一个做法则确实过了份,李监督要求外国商船无偿交出包括自鸣钟表在内的所有奇珍异宝,由他来呈送给皇帝。此举够狠!但英国人不吃这一套,后来的洪任辉事件就是他们的反击。弘历本人被迫卷入此事进行调查和调停。最终的结果:除广州关以外一切对外通商口岸永久关闭!麻烦的李监督在挨了五十大板后也丢了乌纱帽。
值得一提的是,1750年至1792年,粤海关监督一职基本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除了总督衙门会派遣一名武官作为副手外,监督几乎没有直属下级(或者说有想“上位”的下属)。两广总督(两省的最高级别官员)在名义上是粤海关的共同监管人,但海关监督却主管着自己的钱袋,所以总督一般不会插手海关事宜。再者,只有皇帝的奴仆(亲近皇帝的仆人) - 内务府包衣 - 才能担任粤海关监督。此般刻意安排,使到这些与大清皇帝有直接接触的海关监督,在管理任内海关事务,征收税费以及与行商,外国人打交道等方面,不受任何的地方监管!这极大地助长了在位监督的贪婪和他们安抚皇帝的需求。
有一件有趣的事,多处史料显示,许多粤海关监督在到粤上任之前都因为失职而负债累累。而乾隆的御用手段,“自行议罪,自行议罚”(大概意思就是:你知不知道自己错啦?知道啦?好!那我该怎么罚你呢?你说该罚多少!),使得每位粤海关监督一上任就不惜一切地“戴罪立功”!皇帝这套路还是深啊!
上面提到的李监督若不是债台高筑,那就是行事手法确实太low,给再大的权利都无补于事。关于正常的官员让行商购买贡品的情况,范岱克的《广州贸易》里这样写到:
“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散商是携带新奇之物来广州的最重要商人。当他们的船只抵达时,粤海关监督就会迫不及待地冲到黄埔锚地 .... 当具结所有常规货物之后,粤海关监督都会要求“检视”外商带来的“八音盒”(英文叫做sing-songs,自鸣钟另一叫法),以及镜子之类的其他奢侈品。” 他又接着说到:“这些物品往往会成为粤海关监督为保官衔而每年按例呈贡的礼物。在选择最佳物品后,粤海关监督会要求行商购买这些东西。”
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大陆是动荡的,大批为了逃避宗教迫害的新教徒(=劳动力)拥到伦敦,从而助推了英国的工业和钟表业的发展。而喜欢垄断的东印度公司则为这个新兴的产业找到了庞大的市场,装备精良的船队为东西方提供着可靠的物流。大英博物馆的解说员会自豪地向每一位参观者介绍:“在1800年以前,英国的钟表制造业占了全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以上!” 他应该再加上一句:“这里面有一半以上都卖到了中国!!”
就这样,一艘又一艘的西洋货船,源源不断地为大清输送着珍宝,而自鸣钟,可是这珍宝里珍宝啊!

钟表舶来之 - 皇帝的需求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钟表玩家,乾隆,对贡品的要求是促使官员们(包括粤海关监督,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高度关注钟表的第一个原因。故宫前副院长杨伯达先生曾写到:“乾隆一般会收下满意的贡品,然后“发还”不中意的;稍后会口气逐渐严厉,对不满的贡品予以“驳出”,甚至因为贡品不合口味,对进贡的官员加以斥责。” 乾隆十一年,弘历对广东巡抚准泰降旨:“此次所进之物,甚是平常。前曾降旨将紫檀木小香几,格架不必再进,此次仍行进来;再珐琅器皿小瓶亦属太多,牙花珐琅盆景俱不成对。似此俗巧之物嗣后不必再进。”
好家伙,不是极品可忽悠不了我们的大玩家!中国人喜欢东西成双成对的习惯连皇帝也不例外!估计那位巡抚当时就吓尿了。翌年的降旨我们看到了改善:“此次所进镀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后,似此样好看者多觅几件;再有此大而好者义觅几件,不必惜价。如觅得时,于端阳贡几样来。钦此。” 看看这“不必惜价”四个字,真是大玩家的范!
看来那当官的是交过学费了!这次的贡品清单里包括了大小自鸣钟十三架,和一座金镶洋景钟,估计好比今天的好几块限量版的PP!除了皇帝以外,别忘了还有和珅乃至一朝的贪官污吏需要安抚!皇帝的需求变成了官员们的“动力”,再转变成行商们的“压力”.....不难猜测这也就是广府开始自己造钟原因之一吧。为满足皇帝的猎奇心理,广钟后来的技术演变越加妙趣横生,如水法,泛舟,花开,旋转如意,活动人偶等等千姿百态!珐琅背景使用的题材也是精彩绝伦,令人眼花缭乱!关于广钟的话题,需要另草一文和大家聊。
皇帝在时间vs工作效率上的要求是官员们高度关注钟表的第二个主要原因。上面已经提到过康熙的勤政,他甚至在宫内成立了专门研究、维修和制造钟表的工作室,归属到宫廷造办处。与“工作狂”的老爸相比,雍正最多也就差之毫厘,但身体确实不好。故宫内工作效率的提高,必须感谢利玛窦神父和他修筑的巨型自鸣钟。据说该钟原本置于故宫御花园内供大家欣赏,后来康熙下令将其挪到交泰殿里内。一,因为他就住在后面的乾清宫内。大钟一响,钟声传遍包括整个乾清宫及其门外。二,交泰殿是宫内人员和官员们时常出入之地,大钟可既可以为大家报时又可以让大伙校时。
赵翼(清)在他的《檐曝杂记》曾记载一起趣事。皇帝的宠臣博恒,他和别的官员一样随身带有一块怀表,平时都会按照交泰殿的落地自鸣钟给自己的怀表调时上弦。但有一天御门上朝之际,因为自己怀表显示的时间尚未到,所以他休闲从容地走入宫中,不料却被告知皇帝“早已久坐”!WTF?!犹如晴天霹雳,此刻博恒看着手里的怀表深感百般蹉跎,“乃惶悚无地,叩首阶陛,惊惧不安者累日”!估计博恒的内心自责:“嗨!你说你这,多不应该,该花的钱可不能省!早就该托十三行的朋友买个最新款的西洋表,又时髦又可靠!别等这手里的骚货惹毛了皇帝,可就太晚啦!”
于敏中,清朝大臣,曾在宫中军机处任宰辅。他每每听见交泰殿正午的钟声响起时,便会提醒值班的同僚:“表可上弦矣。” 要想在紫禁城里上班,能容易吗!严格按照皇帝钦定的时间表行事,可容不了半点马虎!而于大臣则需要保证在皇帝晚膳之前将奏折呈交上去,一刻的差池,年终奖就有可能泡汤!据说,他是定期会将自己的怀表拿去宫中造办处做维护的,也时常打听钟表贡品的情况以便适时购进新款。
钟表舶来之 - 在民间
综合研判,在B2G(Business to Government)层面,行商充当着为西洋钟表买单的角色。洋人可能也会直接为皇帝送上该年的“新款”;在B2B(Business to Business)层面,行商可能时常要在洋人的漫天开价面前妥协;有时让他们以钟表来抵消某些欠款。但是,奢侈品可是从古至今都广受中国消费者所喜爱的。而正史和多数野史都没有介绍的,是舶来钟表 B2C(Business to Customer)的情况。要了解这个我们要从需求入手。
想想看,和欧洲人做生意特别是英国人,守时是刚需。比如说约定上午10点在夷馆商谈,然后下午2点到黄埔锚地看货,晚上7点到成珠楼宴请等等 ... 商务应酬繁忙的行商对时间的准确拿捏至关重要。所以十三行的商馆内必定有可靠的计时工具,一座大不列颠或者法兰西制造的座钟绝对是镇馆的不二选择!而且功能越多,配置越奢华(什么玛瑙珍珠宝石象牙之类)越能显示该行商的实力。此外各行、各商馆内的大小掌柜,政府指派的大小通事,负责补给品的买办等等,所有在这条贸易链条上形形色色的角色,也是务必身怀一表的。
珠江的水位是受潮汐影响的,十三行所在位置是广州的西关,清代就是一片沼泽浅滩(容易搁浅)。从现存的地名也可略知一二,如黄沙(现在有个水产市场和地铁站)还有沙面(曾经是广州的英法租界)曾经都是沙洲。行商们必须准确地把握潮汐和安排好从黄埔锚地到夷馆码头的航行时间然后紧凑地进行货物装卸,误时就损失。
此外,一个行商的上下游关联商户可以有几十上百家甚至更多。来自全国各地各种字号的茶商,瓷商,布商,经销商等等,还有广州城内的大户,盐商,珠宝商,茶楼老板等等,他们对掌握时间和以钟表显富贵都有刚需。这还没算上那些‘富二代公子哥’‘官二代大少爷’和‘八旗子弟’等诸如此类,形形色色的玩物丧志之士,也必定大有人在。毕竟皇帝之宠,君子欲求。
《红楼梦》第四十五回里曾写到,在大观园里的贵公子贾宝玉“回手向怀内掏出一个核桃大的金表来”。这短暂的瞬间向读者透露了一个信息,康熙时期江浙富商家的公子就已经把玩着舶来的“金表”了。
据 1791年 粤海关记录,该贸易季度进口了大大小小1025件西洋自鸣钟表;而 1793年,乾隆亲自下令购买的自鸣钟表,共计花费超过10万两白银之多!太爽了,简直就是买,买,买不停!石鲸官(而益行)曾是十三行内排行第三的份量级人物,在 1796年却突然离奇地破产。按照惯例,石氏被抄家清算,在官府清点其家产的时候,单单自鸣钟表一项的估值就超过222640两!(备注:当时的物价牛肉一斤是0.09两,猪肉/鸭/鹅0.13两每斤,鸡蛋0.08两一打)
史料记载,行商们时常会因为各种原因被海关监督和行政高官们敲诈勒索。他们会通过“捐输”“捐纳”来换取官衔从而规避一些麻烦(如:体罚或被当众羞辱),此外他们也会储备一定数量的“礼物”尤其是西洋自鸣钟表等以备不时之需。这就解析了为何石氏有如此大量的钟表藏于家中,而他绝非个别。当储备过剩的时候,不难想象一些行商干脆放到店面,连同其他西洋商品一起直接向公众出售。这种场景我们可以从同文街十六号画店关联昌(清)的画笔下感受,他的作品里有同文街售卖钟表和西洋帽子的店铺。

从自鸣钟到怀表
到了十八世纪末期,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学习,复制和创新,中国制造的自鸣钟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英国的进口货。这期间,广州已经向宫廷造办处输送了几代的钟表匠人。凭着拥有来自世界各地一手的珍稀原材料,和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出自广州工匠之手的自鸣钟已是登峰造极。到了乾隆末期,行商和官员已经基本不从洋人手上购买价格过于昂贵的自鸣钟了,而是转向本地采购。1815年,英商 Magniac 与其父亲的通信里写到:“现在已经不能指望像从前那样把自鸣钟卖给中国人了 ... 行商只需用我们一半的价格就能买到一样好的本地钟。” 另外由于生产成本的提高,英国原有的钟表产业无法摆脱手工作坊制的生产模式,最终慢慢地被法国和瑞士的竞争对手以更低廉的价格打败。整个欧洲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怀表变成更多人的需求,就像座机电话变成手机那样,时代吹笙了怀表的普及。
James Cox 和 Jaquet Droz(1721-1790)在中国的成功吸引了大批的欧洲钟表匠人加入到钟表东舶的行列,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William IIbury(1760-1839)。他制造的钟表都使用了自己设计的机芯,为了更受中国顾客的青睐他“创新地”在机芯表面做了精致的雕花,这使原本平庸的机芯表面变得赏心悦目!到后来这些机芯在西方都被称作“Chinese Caliber”,而llbury 则被欧洲的同行们尊为中国怀表教父。IIbury后来收到 Magniac家族的投资并成立了IIbury & Magniac 公司专门向中国出口自鸣钟、怀表和音乐盒等,而正是这个公司在1818年将年轻的Edouard Bovet从伦敦派到了广州。据说,就在 Edouard 到达广州后的不久他就卖掉了4枚名贵的怀表价值约莫今天的1百万美元!等于是25万刀一枚!
除了是一名出色的销售,Edouard 也是一名懂得钟表制造精髓的工匠。他在广州建立了与本地匠人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为他后来在广州成立自己的品牌 Bovet(播威)和独立的生产车间铺下了基石。后来 Edouard 租下了荷兰商馆二楼的一处办公室开始经营自己的品牌,数年后Bovet 变得家喻户晓,几乎占据了以广州(再后来澳门)为据点的整个南中国市场。十二年后,当 Edouard 离开中国时,他已经家财万贯,带着一名华人助手和自己刚出生不久的混血儿子回到了瑞士。他将中国的业务交给了弟弟,再也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余生一直难以释怀自己死于难产的中国妻子。虽然今天该品牌已经不是创始人家族持有,但不过分地说如果没有广州可能根本就不会有播威。1840年鸦片战争席卷而来,中华大地从此卷入长达百年的动乱,而 Bovet,Vacheron Constantin, Jaques Ullmann 等一直在中国市场耕耘的钟表商也像十三行那样慢慢走向式微。

后来
风云变幻大浪淘沙,虽然地方官员甚至整个大清的贪腐是一个打不开的死结,但世事总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在十三行,有人像潘振承那样一代人就成就了辉煌;也有经历两代人才问鼎宝座的伍国莹和伍秉鉴;有像卢观恒那样的奇迹创造者在短短几年时间就从身无分文到跻身行商老大;有功成身退从此不再踏足江湖的叶上林;也有惨淡收场甚至充军伊犁的颜时瑛,张天球和吴昭平等。十三行的兴衰充满了戏剧性,充斥着金钱的诱惑,通过贿赂“购买”特权成为了清朝统治下最大的特色,堆积如山的财富没能阻止国家和人性的衰败。而聪明的英国人利用机械时计提高了自身的生产力和工作效率,大大降低了远洋以及探索航行的风险,改良了军队的作战模式,最后还从中国赚走了很多的钱,成就了日不落的帝国。
中国后来的惨,这里不必多说。这个古老而且富裕的文明经历了洗劫和摧残,新旧制度新旧思潮不停地博弈,战乱纷飞,有人远走他乡,有人含泪死守,而中国内地民间的钟表精品也随着富商财亨们的陨落而流失海外、消耗殆尽。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再度富裕的国人才又拾起了前人的至宝,将之奉为最爱。而在这些钟表爱好者之中,有一小部分人,希望通过自己的笔墨将断弦的往事和趣事分享出来,让大家茶余饭后多些谈古论今的点子,让生活过得更加愉快自在。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