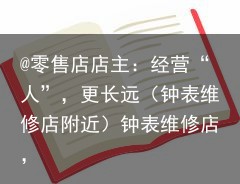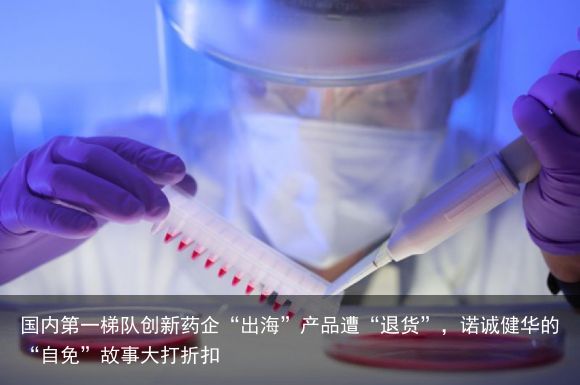软塌塌的钟表像块时间的膏药贴在了谁的痛处?(蚂蚁表演的优美句子)蚂蚁钟表故事视频,
时间的钟表软塌塌的,耷拉在枝衩、桌椅和似鞍非鞍、似马非马上。爱因斯坦之前的世界,钟表和时间都是刚性的,你无法折叠、弯曲,甚至撕裂下一块来耷拉在你的世界里。但现在可以了。
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 1904—1989)的代表作《记忆的永恒》好像不止一幅。他构造了一些他的典型的象征元素:软塌塌的钟表、枝杈、大地、天空、崇山、大海、蚂蚁、蝙蝠等。这些元素,或整体、或分割、或蜕变、或柔软、或碎裂,他经常使用在不同的画幅里。
翻到这一幅,你仿佛发现时间的底色变了。联想至现今,这大约是地球比以前温暖了,人类的体温也由37.5度不算发烧而进化到属于发烧了。
我们把时间撕裂下一块,发现这块发红的钟表上面爬着一群十分清晰、精致的蚂蚁。他们是想搬走时间还是盗走时间?这蝼蚁也要爬上弯曲的时间,几个石头磨过?
被时光冲刷后已变的柔软的钟表搭在枯枝上晾晒。这种柔软可以包裹那块四方方的事物。这是硬核事物,里塞满的或许是钢铁般的知识、智慧、文明、和平,也或许是粘稠的、柔软的愚昧、贪婪、战争、邪恶?
再翻一幅,大地变得更暗。远方的崇山、大海和天空闪着余晖如回光返照一般。恍若隔世,这似鞍非鞍、似马非马,猛然间她一直缺少一位驾驭的主人。
终于,这软塌塌的钟表竟表现出另一面:它是易碎的、已被撕裂了一个口子。它爬上绿头苍蝇。它飞来蛾子。伤口碎片像一行行泪一样泪奔出来。我知道,这个时候,我们的手机已经可以像书页一样折叠,可以像手表一样蜷曲戴在手腕。
我们再抽取出一棵枯枝。枯枝象征一种依靠、一副躯体、一副骨架和一个固定的存在、一个路标。就像我们村口的老槐树,那上面挂了一口钟。钟在枝衩上留了一个缝隙。那是那口钟撕裂的口子没盖得住枝衩。
我和"我"在像一张烤饼一样摊在枝衩的钟的对面面对面。我背着翅膀,"我"穿着长斗篷。这时,枝衩枯木逢春已长出几片绿叶。我知道,那除非是我战胜了"我"。就像二十一世纪战胜了诺查丹玛斯大预言一样。
但是,萨尔瓦多·达利还是不甘心。他又把这块软钟挂上了衣钩。时间就像一件衣服,被一位农妇按在流水的石砧上摩擦、蹂躏、捶打。然后接受阳光的曝晒、紫外线、红外线。
总有一块盖不住的缺口。从那里漏下上下五千年。
我们再割出一块崇山、天空和大海。我们走近一段历史,发现过去的枝衩上挂着现在的巨大的一团白云般的蚕茧壳,而现在的枝衩挂着的是一颗未来的花生和一只远走的鞋子。远走的人地上还丢有他遗弃的碎花生壳
我看过去,那棵枝衩其实已长在我的眉睫,钟还是那般软塌塌的挂着。我看到一群蚂蚁从宇宙深处列队整整齐齐爬进我的眼瞳。
蚂蚁给我们搬来了一个星球的生活。有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有人带自己的孩子远行,有人骑着人像狗一样,有人提着钱袋交易留下累累身影,有鱼上岸了满头红血淋淋,有鱼类被掏干了脏腑丢进垃圾桶,和长着一个鱼形红头,也是红血淋淋的人依偎谈爱情。
这时,萨尔瓦多·达利再次把大地的色调调暖起来。似乎是早晨来临了,天空发出了鱼肚白。
来到割出的一片海岸。海里漂浮着头颅、钟表、哑铃形的一副眼珠。岸上一匹奔马肚子露出了肋骨,丰腴的裸体女人躺在血池旁掩面晒着太阳。一只细长的胳膊丢弃在沙滩。这样的世界,如果抽取出了血腥、屠戮只剩下荒诞,那荒诞是不是比恐怖更可怕。
犹如蛋糕切割出更小一块,进入到一个人类的房间,那时似乎正在做着早餐。炉灶上平底锅的锅里有两个已煎好的荷包蛋。另一个荷包蛋被一根细细的绳索在空中挂着,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荷包蛋像那个软塌塌的钟一样,但这次是个悬着的悬念。东方已有一抹红霞,炉灶的火墙被映的一股红彤彤的铁锈味。炉灶旁似乎有一只半寐趴卧的狗。炉灶的火墙开了个深邃的小窗口,似乎有个人站着在迎接朝阳升起。
另一幅画会带你进入到这个已白昼的房间,太阳完全升起,火墙上映的红彤彤已后移到边沿,下面的炉灶已全部映红。那时你会看到火墙上那个深邃的窗口已大亮,站着的倒背着手的身影已很清晰。软塌塌的钟表挂上了火墙,只是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根弯曲的钟表的指针这次竟然被挑起离开钟体,并在钟体上留下一道指针的影子。没有平底锅了,荷包蛋是从炉灶上的蛋壳里被伸进来的枝杈挂着,也在火墙上留着影子,影子似乎是一条有眼的鱼。那个红透的球体就当是苹果,挂在一个似有非有的枝杈上,它那么巨大,再加上枝头上长出的很大很重的叶子,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没有压弯枝头。更不可思议的还有,这个炉灶似乎就安放在天空下的大海边,四周的天空就是这间房子的墙壁,炉灶前的地上长出粗大的枯枝杈,一直长进炉灶。
年轻美丽的黑发女人,在萨尔瓦多·达利的画像
一根香蕉在四方平板的硬核上站立着背着一身火。只能是这根香蕉被剥了肉,放到桌子上一堆摊开的雪白的棉絮上,这就是一个荷包蛋。荷包蛋又被放到开篇的场景。桌子上、枝杈上、抽屉上耷拉着香蕉皮,枝杈上长着一根香蕉。而另一根大香蕉上耷拉着钟表。一个猴脸人身的走来,他头顶的高高的枝杈上晾着红、绿两只袜子。被七根叉子支起的一根香蕉和海水、远山在水的倒映下恰构成一个打开的蚌。远方的海水上堆积着一道棉花团样的白云。奇怪的是,最前面的抽屉上香蕉的影子怎么看也不是那根香蕉皮耷拉的影子,那会是谁的影子?因为它更像一条弯曲的蛇影。在这里,萨尔瓦多·达利《记忆的永恒》已幻化为《蜕变的永恒的记忆》。
我们所看到的崇山在海水中的倒影,其实这倒影只不过是像挂在远方枝杈上的一块平坦的布单。在这布单下,大地变成一个砖砌的泳池,海水象子弹一样射走。射向鱼类、射向变形的钟表。以往软塌塌的钟表已不再柔软,而是变得僵硬,变成不能复原的硬邦邦的扭曲。似鞍非鞍、似马非马摊在池底,似乎扭曲成一截海底失事飞机的舷窗。又似乎在鱼类的身上也长着这道彩色的舷窗。表象的下面犹如有道巨大的暗网,却只是被一条简简单单的布单盖着。
现在,一个孩子手中正扯着这布单一角,但他双脚凌空,孩子的身影头顶着下面巨大的布单的影子。而一只狗趴卧在布单的影子上,它盯着岛屿的倒影往下伸出了布单,犹如一块肥骨。狗也只是趴卧在布单的影子上噬咬,就算狗代表了一种信仰,但依然触摸不到下面深深的实事和真实。
现在把大地放置一块巨大的盘子,大地犹如一块餐桌。枝杈上不再搭着软塌塌的钟表,而是挂着一个电话、一把伞。发芽的枝滕穿过电话听筒,电话听筒里的声音像液滴一样滴着、一滴即将滴落,细细的挂着一珠滴珠。但人一样的耳廓在另一边。盘子里有几粒花生米,一个花生壳,一个半身相片,相片头像有点像纳粹阿道夫·希特勒。一只蝙蝠飞到盘子边,花生壳伸出一根像蜜蜂一样的针刺对着蝙蝠。蝙蝠旁边还站着一个人,一只微抬的手,一块块肉血淋淋像泥巴一样往下连串的滴。盘子靠前的外面还有小半个花生壳。盘子的后边就是海边,一群小人影在海水边。
就像在你童年、少年和老年不同的色调回到故乡,童年、少年的真实变成了梦境。现在现实生活中根本看不到的景象、离奇的事件、梦呓都历历在目得到了实现。萨尔瓦多·达利创造了一种引起幻觉的真实感。这也许正是超现实主义绘画的真正的魅力所在。
萨尔瓦多·达利的色调变幻、场景切割、事物撕裂应该源于他的内心。幼年时,达利曾因为蚂蚁受到心理创伤:他倾注了全部爱心去救助一只小蝙蝠,最后被一群蚂蚁包围啃咬。达利幼年时形成自卑心理:他在和小伙伴比"小丁丁"的长度时发现了自己的短板,父亲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使他的内心更加扭曲。他因此获得创作上的"超乎寻常的巨大能量",用一种自称为"偏执狂临界状态"的方法塑造了一个个梦幻般的场景,也用天才掩盖自我那一点点小小的"玻璃心"和"和敏感小脆弱"。这让我们得以一窥他真实的欲望世界。
萨尔瓦多·达利1904年5月11日出生在西班牙Figueres的一个小镇上。萨尔瓦多·达利不仅荒诞、离奇的梦境,而且也会极尽搞怪之能事有一份幽默,你看他把自己的自画像抽象成一滩泥,脖子流到台子上,达利作品喜欢枝杈、叉子,叉子撑起眼皮、叉子撑起下巴、嘴唇,撑起脸皮,但你仍旧可以观察到绝对的神似。他与毕加索、马蒂斯一起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有代表性的三个画家。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